|
鲁迅 鲁迅对待中医的态度,是一个颇为值得研究的问题。历来众说纷纭,各执一端,有的认为鲁迅对中医是持批判、否定态度的;有的认为鲁迅对中医是一贯的重视和爱护的;还有的认为鲁迅对中医的认识和态度,随着他的思想的发展,有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发展过程。那么,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一问题呢?其实,鲁迅对中医的态度到底怎么样,这本来是一个不难解决的问题。因为有他的文章在,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得出结论。鲁迅在他的文章中谈到中医的地方很多,时间跨度也很大。最早谈到中医的,是在年12月3日写的《呐喊自序》:“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,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,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,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;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,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”这也是人们常常用来说明鲁迅先生反对中医的有力证据。年1月15日,鲁迅利用自己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便利,于解剖学方面受到了良好的训练和知识,写了《忽然想到(一)》,慨叹中医虽然历史悠久,但缺少一部作为医疗基础知识的可靠解剖学,指出《内经》和《洗冤录》关于人体肌肉构造有不少胡说,以至乱成一片。年10月30日,鲁迅基于自己治牙疼病的亲身经历,写了《从胡须说到牙齿》。说他从小就是“牙疼党”之一,牙齿或蛀或破,终于牙龈流血,留学日本时的鲁迅在中国试尽“验方”,投用单方,看中医,服汤药,都不见疗效,被说是患了极难治疗的“牙损”,但后来到日本的长崎,只花了两元的诊金,用了一小时的时间,医生刮去了牙后的“齿垽”,此后便不再出血了。以后他看中国的医学书,忽而发现触目惊心的学说:齿是属于肾的,“牙损”的原因是“阴亏”。这才发觉了原先别人是在诬陷自己,说出了“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,单方怎样灵,我还都不信”这样的“名言” 年10月7日,鲁迅写了回忆性的散文《父亲的病》。这篇文章,其实是在鲁迅年写的《我的父亲》一文的基础上改编、扩充而成的。《我的父亲》虽然只是五百余字的短篇,但是从少年鲁迅常去为父亲买药的绍兴“光裕堂”药店描写的“我”的父亲临终前的那段情景来看,可以说是《父亲的病》的源作。《父亲的病》约有三千四百字,比起《我的父亲》篇幅要多出六倍以上。而其增加部分大半是对中医的冷嘲热讽。最先来给鲁迅父亲看病的“某个名医”,是位出诊费极高的人物,据说他曾给一个城外人家的闺女看病,只是草草地一看,说了些“不要紧的”之类的话,结果给治死了。就是这个“名医”给鲁迅父亲治了两年病,可病情却是不断地恶化而没有一点好转,到最后,他推荐了另一位叫陈莲河的医生而自己离去了。于是在这位陈莲河医生的方子里,就有了“原配同巢”的“蟋蟀一对”,“谁都不知道的”“平地木十株”以及用打破的旧鼓皮作的“败鼓皮丸”等药引。关于蟋蟀,鲁迅又加以讽刺地说:“昆虫也要贞节,续弦或再醮,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。”对“败鼓皮丸”他也附以说明道:因为父亲的病是“水肿”,别名“鼓胀”,所以“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”。从上面的摘引中,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,鲁迅对中医是抱有成见的,甚至是颇为反感的。当时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所做一副对联:“爬山、吃肉、骂中医,年老心不老;写字喝酒说官话,知难行亦难。”可见,骂中医当时的大气候,也是当时自诩为新潮人士的共识与共举。而西医刚传入中国,新娘三分香,就更为得宠,将西医视为科学的楷模也就天经地义。尤其是,由于中医的深刻与玄妙,表面看来确乎与科学有距而与迷信有染,视中医为迷信也就“顺理成章”了。 然而,鲁迅先生对中医究竟是什么态度呢?鲁迅先生虽然留学日本,但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理解亦是比较深刻,从他写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可见一斑。他对中医的批判也给出了理由:“到现在,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,单方怎样灵,我还都不信。自然,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,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。”要知道他父亲的“鼓胀”病,西医在当时可以说是束手无策的,是不治之症,即便在西医高度发达的今天,也是难治之病。因为中医“医死”了他患有“不治之症”的父亲,就“挟带私怨”说中医是“骗子”,这符合鲁迅的风格,但并不意味着他对中医全盘否定的。 鲁迅在杂文《经验》中,对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给予了充分肯定,进而认为医药不是圣贤所创造的,而是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斗争的总结:“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,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。建筑,烹饪,渔猎,耕种,无不如此;医药也如此。”从这一段话里,我们可以看出鲁迅认为在中医中药中虽然有“捕风捉影”的地方,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中医中药是历来许多无名氏经验的积累,它和建筑,烹饪,渔猎,耕种一样,从很早的时候起,就为我们服务,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它是什么“封建医学”。而鲁迅在上海的时候,常常和周建人先生相见,兄弟俩在茶余饭后,总有谈话。谈话内容,其中就会从植物学谈到《本草纲目》或其他中医如以生草药治急病见效等的,也非常称赞《验方新编》上的一些药方,曾经亲自介绍一位朋友用它治疗孩子的疝病。 鲁迅所批评的,只是那些道德低下、作风恶劣、开方荒诞不经、治疗无效时推给鬼神了事的中医,鲁迅对这些落后迷信现象无情加以揭露和批判,应是无可非议的。在《父亲的病》中提到的“某为名医”“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,特拔十元,深夜加倍,出城又加倍”,而且出门必须坐轿,进门必须烟酒相待,必恭必敬,深有“请医如拜相”的味道;所用的药物,如冬天的芦根,经霜三年的甘蔗,结子的平地木,打破的旧鼓皮,这些对水肿病究竟能起多大作用?蟋蟀用来当作药物也就罢了,为什么还要“原配”呢?原配与治病有什么关系?而且更甚的还有什么“医者,意也”的附会,和“医能医病,不能医命”的迷信观念。要知道当时2块大洋是普通人家一个月的开支,而鲁迅作为一个落魄家庭的长子,他因为父亲的病“有四年多,曾经常常——几乎是每天,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……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手饰去,在侮蔑里接了钱,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……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”不但自己被弄得狼狈不堪,而且家庭也由“小康”而坠入“困顿”。这些惨痛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,在幼年鲁迅的心里,曾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,所以后来对中医中药不合理的地方才有过一些批评。是不是颇有现在“医闹”的作风?只不过现在“医闹”用的是“打砸闹”,用的武器是刀,而鲁迅用的是笔 鲁迅在日记中,多次写到服用中药的经历。年11月10日,“饮姜汁以治胃痛,竟小愈”。同年11月23日,“下午腹痛,造姜汁服之”。年4月22日,“晚因肩痛而饮五加皮酒”。年8月30日至9月6日的八天日记里,有四次写到为儿子周海婴前往仁济堂购买中药。并且鲁迅也曾阅读收藏并亲自动手修补中医药书籍,在《鲁迅日记》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:年9月12日“买《备急灸方附针灸择日》共二册”,年2月21日“买景宋《王叔和脉经》一部四本”,同年2月26日“购到《巢氏诸病源候论》一部十册”,4月27日“买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一部二本”,年8月2日“买《六醴斋医书》一部二十二本”。鲁迅不仅亲自到书店选购中医书,而且还自己动手修补中医书籍。年8月12日的日记写道:“下午修补《六醴斋医书》。”8月17日“下午修补《六醴斋医书》讫”。试想,如果鲁迅先生对中医药怀着偏见眼光的话,他还会如此长期地购买阅读钻研这些祖国医学典籍么?如果说收藏中医古籍是为了创作需要,那么动手修补中医古籍则是对中医的一种肯定。 据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在回忆录《非凡书房:鲁迅与我七十年》一书中说:“曾有人著文,说鲁迅反对中药,鲁迅与周海婴更不信中医。实际似乎并不如此。”他还列举出了当年母亲许广平服用乌鸡白凤丸的事例:“母亲当时因过度劳累,白带颇多,西医让用冲洗方法,没有见效。她遂买‘乌鸡白凤丸’服了,见效很快,连西医也感到吃惊。这种中药丸,后来父母亲还介绍给萧红服用,因她也是体弱劳累,生活不安定,以致患了妇女的月经不调症,结果也治愈了。” 虽然鲁迅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,但他并不是全盘反传统主义者,并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,鲁迅反对的是传统文化的负面性。鲁迅即使在批评中医的年代里,仍在读中医之书,用中医之法,感受中医之效。可见,鲁迅对中医学并非全盘否定,而只是抨击其中的糟粕。随着年岁的增长、阅历的丰富,能更全面、深刻地认识事物,从而也看到了中医药的真正价值和贡献,鲁迅对中医的态度,大约的确已经改变了。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:http://www.gbokw.com/kjscyf/25938.html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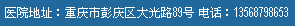 当前时间:
当前时间: